蒲松龄,清代著名文学家,以其奇幻诡谲的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而名垂千古。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丰富的想象力,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瑰宝。然而,细读《聊斋志异》,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蒲松龄在书中并非以作者的真实身份出现,而是选择了用一个特殊的“我”来代指自己。那么,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是如何自称的呢?这背后的创作心态又是什么?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自称
一、书中“我”:一个隐秘的观察者
在《聊斋志异》中,蒲松龄以“我”自称,但这个“我”并非作者本人,而是故事中的叙述者,一个隐秘的观察者。他游走于人鬼妖之间,亲身经历或听闻各种奇闻异事,并将它们娓娓道来。例如,在《狼》中,蒲松龄以“我”的身份描述了狼的狡诈凶残,以及它与人类之间的恩怨情仇。在《画皮》中, “我”则化身一名落魄书生,亲眼目睹了狐妖的魅惑与欺骗。
这个“我”身份的隐秘性,赋予了《聊斋志异》独特的叙事视角。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奇幻世界,与“我”一起见证了人间百态,感受了人性的复杂与美好。同时,也为作者表达内心想法提供了隐蔽的空间,使他能够在不触犯封建礼教的情况下,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。
二、自称背后的创作心态:隐喻与讽刺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自称“我”,并非简单的叙事技巧,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。这背后折射出他独特的创作心态:
1. 隐喻现实,借鬼说人: 蒲松龄生活在清初,当时的社会环境复杂,政治腐败,民生凋敝。他无法直接批判现实,便借鬼神故事隐喻世相,借妖魔鬼怪讽刺人性的丑恶。例如,《促织》中,主人公为求功名而逼迫儿子捕捉蟋蟀,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。这个故事隐喻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残酷,以及人们对功名利禄的盲目追求。
2. 追求自由,表达自我: 蒲松龄虽然出身书香门第,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。他深感世俗生活的束缚,渴望自由和独立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中,他通过塑造“我”这个身份,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解放出来,进入一个不受拘束的奇幻世界,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。
3. 反思世道,警醒世人: 蒲松龄通过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,探讨了人与鬼、人与妖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揭露了人性中的贪婪、虚伪和自私。他以独特的视角反思世道,警醒世人,希望人们能够明辨是非,保持善良和正义。
三、创作心态的延续:后世对“聊斋”的解读
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自称“我”的创作手法,不仅成就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,也影响了后世对《聊斋志异》的解读。后世学者对《聊斋志异》的研究,往往会从“我”这个身份出发,分析其背后的隐喻、讽刺和寓意,并将其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。
例如,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就对《聊斋志异》的创作背景和作者心态进行了深入分析,认为蒲松龄的创作“含有讽刺之意,而其深意则隐于鬼狐之中”。
总而言之,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自称“我”,并非简单的叙事技巧,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。这背后折射出他独特的创作心态:隐喻现实,借鬼说人;追求自由,表达自我;反思世道,警醒世人。正是这种创作心态,成就了《聊斋志异》的文学价值,也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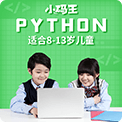








 浙公网安备
33010802011855号
浙公网安备
33010802011855号